
 Librerأa Perellأ³ (Valencia)
Librerأa Perellأ³ (Valenc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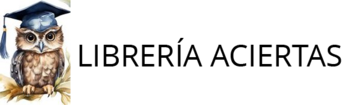 Librerأa Aciertas (Toledo)
Librerأa Aciertas (Toledo)
 El AlmaZen del Alquimista (Sevilla)
El AlmaZen del Alquimista (Sevilla)
 Librerأa Elأas (Asturias)
Librerأa Elأas (Asturias)
 Librerأa Kolima (Madrid)
Librerأa Kolima (Madrid)
 Donde los libros
Donde los libros
 Librerأa Proteo (Mأ،laga)
Librerأa Proteo (Mأ،laga)
çœںو£و„ڈ義ن¸ٹçڑ„ه¯«ن½œï¼Œç¸½وœƒه†’çٹ¯هˆ°ن¸€ن؛›ç¦په؟Œï¼Œç„،è«–وک¯و”؟و²»ن¸ٹçڑ„,ه€«çگ†ن¸ٹçڑ„,還وک¯ç¾ژه¸ن¸ٹçڑ„,這وک¯و–‡ه¸è‡ھè؛«çڑ„é‚ڈ輯ن½؟然م€‚é‚£é؛¼ï¼Œهœ¨ن¸€ه€‹ه¾Œو¥µو¬ٹو„ڈèکه½¢و…‹ن¸‹ï¼Œç•¶ن»ٹçڑ„ن¸هœ‹è‡ھç”±ه¯«ن½œè€…هڈھè¦پéپ¸و“‡'è‡ھç”±'ن½œç‚؛ه¯«ن½œçڑ„ه”¯ن¸€و¨™و؛–çڑ„話,ه°±ه؟…然وœƒه†’çٹ¯و”؟و²»çڑ„ç¦په؟Œï¼Œوˆگç‚؛ن¸€ه€‹و”؟و²»ن¸ٹçڑ„'ç•°è°è€…'ه’Œ'ه°چوٹ—者'م€‚و£ه¦‚ه¸ƒç¾…茨هں؛و‰€èھھ'و–‡ه¸ه؟…é ˆه¹²é گو”؟و²»ï¼Œç›´هˆ°و”؟و²»ن¸چه†چه¹²é گو–‡ه¸ç‚؛و¢'م€‚ن½œه®¶و±ن؛çڑ„هڈ¯è²´ن¹‹è™•ه°±هœ¨و–¼ن»–能çھپç ´è‡ھè؛«çڑ„ه¯©وں¥ï¼Œه°‡è‡ھه·±و”¾هœ¨و›´ç‚؛ه»£é—ٹçڑ„è‡ھç”±ن¹‹هںں,ه¾è€Œن½؟ه¾—ن»–能ه¤ ç›´é¢و°‘و—ڈéپژه¾€çڑ„و‚²و…که’Œçڈ¾ه¯¦çڑ„èچ’謬,ن¸¦ن»¥é«ک超çڑ„و–‡ه¸é€ è©£ه’Œç½•è¦‹çڑ„良çں¥èˆ‡ه‹‡و°£وٹٹو–‡وœ¬ï¼ˆه°±هœ‹ه…§ه°ڈèھھو•´é«”و°´ه¹³è€Œè¨€ï¼‰وژ¨هگ‘ن؛†ن¸€ه€‹ه‰چو‰€وœھوœ‰çڑ„é«که؛¦م€‚這و¨£ن¸€ه€‹ن½œه®¶ï¼Œن»–ن¸چهƒ…çٹ¯ن؛†é€™ه€‹و™‚ن»£çڑ„ه؟Œï¼ŒهگŒو™‚ن¹ںçٹ¯ن؛†é€™ه€‹و™‚ن»£وµپè،Œçڑ„çٹ¬ه„’ن¸»ç¾©è€…--精緻هˆ©ه·±çڑ„'è¥ ن¸‹ن½œه®¶'ه€‘--çڑ„ه؟Œم€‚ن»–ه€‘ن¸چو•¢و–¼ç™¼ه‡؛è‡ھç”±çڑ„èپ²éں³ï¼Œه°±ه؟…然ه°چو–¼و–‡ه£‡é‚ٹç·£و‘¸çˆ¬و‰“و»¾çڑ„و¥µه°‘و•¸'و±ن؛'ه€‘ه½¢وˆگن¸€ه€‹'ه£“هٹ›هœکé«”'[1]م€‚هœ¨é€™è£،,وˆ‘وƒ³èھھï¼ڑه°±è®“é‚£ن؛›èپ°وکژن؛؛éڑ¨è‘—這ه€‹èچ’謬çڑ„و™‚ن»£هژ»ç›،وƒ…çڑ„ç؟»و»¾هگ§ï¼پم€ٹو—¥و™·م€‹هƒ…هƒ…هڈھوک¯ن¸€ه€‹é–‹ç«¯ï¼Œو¼«و¼«é•·ه¤œï¼Œهœ¨ç•¶ن¸‹çڑ„ه¾Œو¥µو¬ٹو„ڈèکه½¢و…‹çڑ„ه¤©ç©؛ن¸‹ï¼Œé€™éƒ¨هڈچو¥µو¬ٹه°ڈèھھوک¯é›£ن»¥é€ڑéپژه‡؛版ه¯©وں¥هˆ¶ه؛¦و£ه¼ڈه‡؛版çڑ„م€‚這ن¹ں許و£وک¯ن½œه®¶و±ن؛çڑ„و¦®è€€ï¼Œه› ç‚؛ن»–é¢هگ‘çڑ„وک¯وœھن¾†م€‚ [1]آ آ آ آ ه£“هٹ›هœکé«”وک¯وŒ‡é€ڑéپژç²¾ç¥ه£“هٹ›è؟«ن½؟ه€‹é«”و”¾و£„ه€‹ن؛؛و„ڈé،کن»¥ه’Œهœکé«”ه…¶ن»–ن؛؛ه“،هڈ–ه¾—ن¸€è‡´و„ڈ見çڑ„هœکé«”م€‚ه®ƒهˆ©ç”¨هœکé«”وˆگه“،ه°چو¸ه±¬و„ںه’Œن؛¤ه¾€çڑ„需و±‚,ن½؟ه€‹é«”و“”ه؟ƒè‡ھه·±هڈ—هˆ°ه¤ç«‹م€پوژ’و–¥ه’Œه”¾و£„,ه¾è€Œه¯¦çڈ¾هœکé«”و„ڈ見çڑ„çµ±ن¸€م€‚هœکé«”ه£“هٹ›éپژ程由ç¾ژهœ‹ه؟ƒçگ†ه¸ه®¶ه“ˆç¾…ه¾·آ·èگٹç¶ç‰¹و–¼1972ه¹´وڈگه‡؛,ن»–èھچç‚؛هœکé«”ه£“هٹ›éپژ程هˆ†ه››ه€‹éڑژو®µï¼ڑçگ†و€§éڑژو®µم€پوƒ…و„ںه¼•ه°ژو®µم€پç›´وژ¥و”»و“ٹéڑژو®µه’Œé–‹é™¤èƒŒé›¢è€…éڑژو®µ